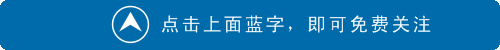
这些年来,有两个看上去互不相关的“将军轶事”,一直深深地在我脑海里萦绕。
(一)
第一件事来自罗瑞卿将军小女儿罗点点的回忆。1973年,还没有完全解除监禁的罗瑞卿住进301医院,他没有想到另一个被监禁的彭德怀元帅和自己关在同一个走廊里。罗瑞卿若有所思地对女儿说:“不应该把我和他关在一起啊,彭德怀还是做了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来和他比?”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拍案而起仗义执言,结果被罢官撤职,定性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罗瑞卿本来就对彭德怀有成见,此时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高调“反彭”。庐山会议后,罗瑞卿升任总参谋长,权倾一时。
没想到,时隔仅仅六年,1965年底,罗瑞卿被突如其来的“上海会议”整肃,后来也定性为“反党集团”。文革爆发后,彭、罗二人惨遭造反派批斗,受尽精神和肉体的摧残。1973年年底这些天里,一同住在301医院同一个走廊里的罗瑞卿和彭德怀二人, 即“同病相怜”又“同命相连”。
后来,罗瑞卿知道彭德怀患晚期癌症,吃不下饭,在病房里痛得喊叫,他忽然难过地对女儿说:“你知道吗?这个人是没有孩子的。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来看他。”很多人都知道,彭德怀和罗瑞卿之间一直结怨甚深。
不过,此刻罗点点突然想到:这两个一辈子也没能很好互相理解的倔强的人,此时此刻,在一种柔软温和的人性恻隐地带,他们的心倒是相通了。(摘自罗点点:《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十月版,251-252页,152页)
(二)
第二件事与前海军政委苏振华上将有关。1976年年底,粉碎“四人帮”不久,苏振华受命坐镇上海。在一次会议结束以后,“四人帮”在上海的主要亲信徐景贤突然表示有一件事要单独汇报。他说,张春桥曾想和自己的妻子离婚并婉转地托徐景贤在上海找一个异性伴侣。后来由徐一手操作物色到一位条件适合的单身女士,徐在1976年10月6日那一天亲自将这位女士的材料和照片寄给在北京的张春桥。
没想到,就在这一天,张春桥在中南海怀仁堂被华国锋逮捕羁押。估计徐景贤此刻只想着戴罪立功,他当面问苏振华等中央工作组的几位领导:“我要不要当众揭发这件事?”
此时一头白发的苏振华,双目炯炯,一板一眼地说:“这件事,我看就到此为止。不要搞什么当众揭发了,人家(指女方)并不知道嘛,不要闹出一条人命来。”
最后,苏振华对徐景贤看了一眼,再次斩钉截铁地说了四个字:“到此为止。”有人后来设想,如果这件事遇到另一位铁石心肠的将军,这样的事还是会“一查到底、绝不手软”的。
这个女人是谁?至今无人知晓,很可能就因为苏振华的“到此为止“这句话成为千古之谜。为什么苏振华此刻可以斩钉截铁地说出“此事到此为止”这句话?如果多少知道一点儿苏振华个人婚姻家庭情况的人,大概会容易理解。
60年代初,时任海军政委的苏振华突然遭遇家庭变故,他被迫与妻子离婚(据他子女回忆,是他的前妻先离家出走,提出离婚)。后来,苏振华娶了比自己小22岁的海政文工团舞蹈演员陆迪伦(在电影《红珊瑚》中扮演过角色)。
在文化大革命中,苏振华夫妇饱受劫难。1967年1月,苏被造反派绑架并关押,当时造反派声讨苏振华的一个重要罪名就是所谓“喜新厌旧,离婚娶了个年轻女演员”,苏振华在被关押期间遭受非人拷打,被打得鼻青脸肿,口冒鲜血,门牙打落、手指折断,膝盖露出白骨,几乎被活活打死。
他的妻子因受牵连,文革期间在海军大院被造反派屡次批斗、毒打和羞辱。1976年,当苏振华将军面对徐景贤检举中涉及的某位无辜女子时,也许他的脑海里正浮现出自己年轻的妻子陆迪伦在文革期间那悲惨屈辱的面容。
正是由于乱世,人性中的所有侧面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然而,也正是在乱世沉寂后,没有比自身的苦难更能让那些曾经久经沙场、铁骨铮铮的人们萌生人性中宽容和怜悯的情愫了。
在为数众多的“红二代”群体中,罗瑞卿的小女儿罗点点大概多少有些另类。在她的笔下,常常流露出某种这一群体中难得的 —— 能超越意识形态的悲天悯人的深刻反思。
改革开放后,罗点点知道潘汉年的冤案和胡风的冤案都是自己当年担任公安部长的父亲亲自奉命执行的。她后来发现:“胡风的妻子梅志当年奔走的那条通往秦城监狱的路,11年后,在那条路上奔走的是我们 —— 当年公安部长的儿女们,迎着同样刺骨的寒风,心头重压着同样的生离死别的痛苦。”
遗憾的是,多少年来,能够将这两个悲剧的份量加在一起思考的“红二代”们,实在少得可怜。他们的父辈们曾无情地整肃过别人,而后又被别人更无情地整肃,但是他们其中有不少人,至今还没有走出那个给家国天下以及他们的家庭带来灾难的“血色阴影”。
在人类情感演化的阶梯上,无论是政治党派血战的复仇,还是内部权力斗争的倾轧;无论是意识形态分歧的愤懑,还是争名夺利的嫉妒等等,其实这些都只不过是一类最低层的物竞天择活动,最细腻精致的意识(包括潜意识)一定属于那些凭借个体体验而得知的超越狭隘的“宽容和怜悯”意识,这类高层次的情感无疑可以扭转人性中看上去不可救药的暴力和异化倾向。中国古人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或许说的就是这类道理。
费孝通先生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 (见《读书》杂志1999年第12期,第24页)。我以为,这种说法多少属于对儒家文化一厢情愿的溢美之词。恻隐、怜悯、同情、博爱、善良、仁慈这些人类心灵中最珍贵的东西,恰恰是我们这个民族十分稀缺的财宝。
长期以“阶级仇、民族恨”为核心的畸形文化,对国人的心智异化甚深。在人类不断进步的二十一世纪,有些国人在为美国“911”恐怖主义袭击带来几千无辜平民的死难而鼓掌喝彩,有些国人在为“311”地震海啸夺去成千上万日本人的生命而幸灾乐祸,回眸或举目所至,在我们中国人生活的社会里,这类能够推己及人的“宽容和怜悯”意识,实在还有太多的发展空间。
(三)
阅读过亲历文革重大事件的吴法宪写的回忆录,其中谈到文革中江青对待戚本禹两个未成年子女的态度。书中提到,1968年,文革中曾红极一时的戚本禹突然在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被江青下令逮捕关押。
江青事后又说,戚本禹的老婆也是坏人,把她也一起抓起来。但当时戚本禹夫妇家里留有两个才五、六岁的孩子无人看管。江青提出让军队负责代管。吴法宪奉命先将这两个孩子放在北京郊区某军用机场,但江青知道后十分不满,再次厉声下令:“把他们送远一点儿”。
于是这两个幼小的孩子被送往青海高原某个偏僻的空军营地。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后来的命运到底如何呢?人们至今不得而知。
前不久,有些怀念文革的“网络乡民”们,提出应当奉江青这个“前第一夫人”为“国母”。且不谈江夫人在文革期间的其他丧尽天良的劣迹,仅凭她对待这两个无辜幼童的粗暴态度 —— 既无常人之恻隐,又无母性之阴柔,这样的女人可以做我们的“国母”吗?
1966年8月,文革期间,北京大兴县发生了对所谓“四类分子”及其家属没绝人性的大屠杀,仅仅6天的时间里,该县的13个公社48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包括年过八旬的老人和刚刚满月的婴儿。
有目击者后来回忆,在大兴县X村,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当凶手们向他们身上扬土时,被抱在奶奶怀里的小男孩还不懂得马上要发生的事情,他说:“奶奶,迷眼。”老人无奈地对孩子说:“听话,一会儿就不迷了。”
我们大致可以相信,当年那些一锹一锹地向被害者身上扬土的凶手们,如今大部分人还都活着,当然还包括那些毒打彭德怀、罗瑞卿、苏振华的人,包括那些当年将自己的老师活活打死的中学红卫兵们,还包括那些为了表明大义灭亲反戈一击而痛打自己亲生父亲的人。
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没有良心的忏悔,更少有痛彻的反思,也许如今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或身居高位,或腰缠万贯,但他们最缺少的却是心灵的救赎。
文革已经成为昨日的梦魇,但它的幽灵从未远去,或许有一天会再次降临中国大地,即使是以改头换面的方式。面对今日中国的现实,假如有人向我们保证,文革种种将“到此为止,下不为例”,你相信吗?
这是作者为《法制日报-法治周末》撰写的专栏文章
赞 赏
(觉得文章不错就点下赞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