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刊于《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23-28页。
已获作者授权推送,特此致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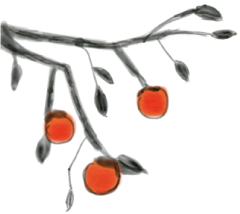
[摘 要] 20世纪以来,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禅文化也已逐渐走出汉文化圈,在英语世界中广为流传。但与儒、道文化不同,禅文化最初由日本学者传入西方,并被鼓吹为日本文化的精髓,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英语读者只熟悉禅的日语发音“Zen”,而不知道来自汉语的 “Chan”。文章将以时间为经,以“Zen” “Chan”在英语中的语义变化为纬,讨论“禅”在英语中的指称演变史。主要内容包括早期“Zen”在英语世界中广为流传背后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Chan”的苏醒和崛起,以及“Zen” “Chan”之争对争夺文化话语权重要性的启发。
[关键词] 禅;Zen;Chan;文化话语权;铃木大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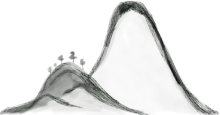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禅文化西渐进程中《六祖坛经》多模态译介研究”(18CYY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于海玲,女,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翻译学博士,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六祖坛经》英译、多模态与翻译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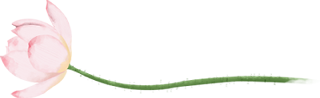
一、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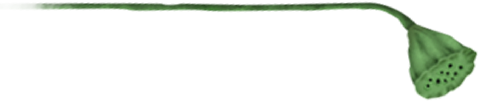
近年来,如何更好地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文化话语权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话题。文化话语权的重要性和提升路径,中华传统文化在增强中国文化话语权过程中的重要性都已经得到广泛讨论[1]。这些研究告诉我们,文化话语权不是某一文化自然享有的,而必须通过主动建立和与其他文化竞争而获得。另一方面,鉴于英语的全球影响力,以英语为媒介的文化传播必将成为各国文化话语权争夺的焦点。
在已有宏观理论性探讨的基础上,本研究将主要关注微观层面,聚焦学界尚未有涉及的中华禅文化。与儒、道文化不同,禅文化最初由日本学者传入西方,并被标榜为日本文化的精髓。本文将系统梳理“禅”这一术语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史,并就其目前所使用的两种表达方式,即来自日语的“Zen”和来自汉语的“Chan” (Ch’an),讨论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文化话语权的流失,以及新时代文化自信背景下如何提高文化话语权意识。
禅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思想融合的结果,代表着佛教中国化的最高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太虚法师曾指出,“禅宗者,中国唐、宋以来道德文化之根源”[2],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禅在中国产生、发展之后,大约于公元6世纪传入越南,7世纪传入朝鲜半岛,12世纪传入日本,对东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3]。中国的“禅”在越南被称为Thiên,在朝鲜被称为S?n,在日本被称为 Zen。而这些不同的名称中,来自日语的“Zen”在英语世界中最为流行,也成为唯一一个被录入《牛津英语外来语精要辞典》[4]中的“禅”的英文指称。那么,“Zen”在英语中的流行是否仅因为禅最初由日本人传入西方?“Zen”到底能不能作为“禅”的英文名称?基于汉语拼音的“Chan”又能否使用?“Zen”与“Chan”之争对新时期文化自信背景下文化话语权的建立和增强又有何启发?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尚未有学者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本文将以时间为经,以“Zen” “Chan”在英语中的语义变化为纬,讨论“禅”在英语中的指称演变史。主要内容包括早期“Zen”在英语世界中广为流传背后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Chan”的苏醒和崛起,以及“Zen” “Chan”之争对争夺文化话语权重要性的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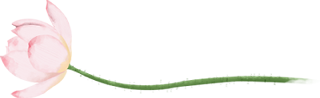
二、“Zen”在英语世界中的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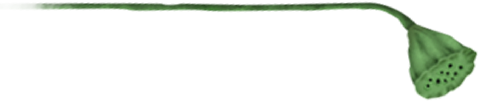
(一)“Zen” 进入西方:成功的开端
1893年9月,美国芝加哥召开“世界宗教大会”,为有史以来参加人数最多、代表流派最为广泛的一届宗教盛会。在这次宗教大会上,来自日本的临济宗大师释宗演(1856—1919),做了“仲裁,而非战争”(Arbitration Instead of War)和“佛教的因果论”(The Law of Cause and Effect, as Taught by Buddha)两个发言。释宗演的发言成功引起了一些与会美国代表的兴趣,打开了随后日本禅顺利进入西方的大门。
这一事件看似偶然,背后却是日本佛教徒处心积虑将日本佛教文化向西方传播的周详计划。明治维新(1868—1912)初期,日本政府推崇神道,佛教被认为是外来的迷信思想,受到排挤和破坏。排佛运动顶峰时期的废佛毁释运动给日本佛教带来了进一步打击[5]。面对这一危机,日本佛教中的有识之士开始积极寻求应对之策,其中包括积极进行海外推广,努力使佛教成为独立宗教,以及提倡“护国爱教”,加入建构帝国政治意识形态的主流[6]。作为佛教改革的坚定拥护者,释宗演在年轻时就主动学习西方文化、科技知识[7],为日本佛教的西方传播做准备。因此,释宗演在世界宗教大会上的演讲可谓知己知彼,准备充分。一方面,基于他对西方基督教的了解,释宗演采用了一种有助于在场基督教徒易于理解的言说方式,且对西方的文化典故顺手拈来。另一方面,对同时代西方思潮的准确把握也使得释宗演可以有的放矢,针对当时人们对佛教的指责和偏见进行一一反驳[8]。“仲裁,而非战争”这一发言所面对的是各国佛教代表,其主题是宣扬和平友爱,批判战争。《佛教的因果论》这一发言则针对所有与会代表,运用西方人所熟悉的推理方法对佛教因果论进行了论证。在发言在中,释宗演声称,因果轮回为人类提供了天堂与地狱之外的其他可能[9]。
释宗演的发言极为成功,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极好的、难以忘怀的印象”[10]。大会期间,美国比较宗教学家、哲学家、作家、编辑保罗?卡鲁斯(Paul Carus)即与释宗演进行交谈,请释宗演协助翻译一些有关东方思想的书籍。释宗演向卡鲁斯推荐了他的学生,铃木大拙贞太郎 (D. T. Suzuki)。释宗演在宗教大会结束后即返回日本,但他在1905年应邀重新访美,在美国多所大学进行演讲,与美国佛教徒进行交流,并参观了一些禅学中心。释宗演1905至1906访美期间的演讲由铃木大拙整理并翻译,以《一个佛教僧正的法话集》(Sermons of a Buddhist Abbot),后改为《向美国人讲禅》(Zen for Americans)为题出版。
尽管释宗演在世界宗教大会上的发言至今仍为日本学者所津津乐道,但毫无疑问,他对于“Zen”西传最大的贡献在于将铃木大拙送到了美国。铃木大拙于1897年抵美,担任卡鲁斯的翻译和助手,直到1909年返回日本。他一生致力于日本禅宗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著述颇丰。由于其对西方文化和思想颇为熟悉,采取了易于为西方人所接受的书写策略,铃木大拙的作品广受欢迎,被誉为向西方传播禅宗的第一人。
(二)“Zen”的语义演变:中国禅的升华和日本文化的精髓
与佛教其他流派进入西方不同,早期西方读者认识禅,大多是通过铃木大拙为代表的日本学者的英文著作。中国学者话语权的丧失和西方本土历史学家和文字学家的集体失声,导致了大量偏见和在民族主义情节操纵下对历史的刻意扭曲先入为主,占领了早期西方读者的思维。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盛行,对外侵略扩张蠢蠢欲动。大量日本佛教学者积极向国家意识形态靠拢,一方面将禅与武士道精神捆绑,煽动普通士兵参战热情;另一方面急欲树立日本禅独一无二、高高在上的“完美”形象。然而, 即使是最顽固的民族主义者,也无法否认禅起源于中国这一事实。在民族主义的操纵下,日本学者采取了另外一种策略,即向西方读者宣称,中国禅在传入日本之后就已经消亡,日本禅(Zen)是当今世界上仅存的、最纯粹的禅。
1906年,仍在担任卡鲁斯翻译助手的铃木大拙发表了题为《佛教禅宗》(The Zen Sect of Buddhism)一文,开篇便写道,“在远东的众多佛教流派中,有一个流派尤为与众不同……这一流派的学名为佛心宗,但更为流行的名字是Zen(巴利文中是Jhana,汉语中是Shan,梵文中是Dhyana)”[11]。在叙述早期禅在中国的发展时,铃木大拙写道:“六祖惠能所领导的南派传承了正统,在其发源地[中国]早已不再活跃,实际上已经灭亡,却依旧在日本繁荣发展。”同样,1913年,铃木大拙的朋友,日本曹洞宗大师忽滑谷快天在哈佛大学讲学期间写成《武士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the Samurai)一书。书中声称,佛教在其他东亚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了。禅宗是佛教一个古老的流派。“纯粹的禅宗”如今只存在于日本[12]。
除了声称禅在现代中国已经消亡,日本学者还向西方读者宣称,中国禅与日本禅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中国人只是给予了禅最初级的形式,禅的内核是在禅宗思想与日本精神结合之后才产生的。中国禅只存在于寺庙和僧人之间,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没有产生影响。在禅由中国传入日本之前,日本人就已经在过一种“禅一样”的生活了。禅的传入恰好触发了日本人固有精神的升华,从而催生了独一无二的、最纯粹的“日本禅(Zen)”[13]。铃木大拙影响较大的《禅与日本文化》一书[14], 更是将禅与日本武士道、剑道、茶道、文学紧密相连。禅的中国起源被贬低、弱化,禅一跃成为日本文化的精髓。
就这样,“Zen”摇身一变, 不再仅仅是中国禅在日本的一个分支,而成为日本民族精神作用下对中国禅的继承和升华。禅在古老中国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历史所做的漫长铺垫,只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在合适的时机传入日本,与日本传统思想和文化相结合,创造出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日本禅(Zen)。“Zen”所代表的(日本)禅是近两千年汉传佛教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汉传佛教智慧的集大成者。
(三)“Zen”的语义扩张:“禅”的代名词
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50、60年代,“Zen”在美国社会的影响进一步深入。50年代初,“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杰克?科鲁亚克,艾伦?金斯堡,盖瑞?斯奈德等纷纷从禅宗文本中汲取灵感,催生了与美国本土文化交融后产生的“垮掉禅”(Beat Zen)。1951年,铃木大拙重返美国,在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主的多所大学巡回讲学。他的公开讲座经常吸引来自文学、艺术、文化等不同领域的学者。1958年,美国文学期刊《芝加哥评论》第12卷2期登载了一系列以“Zen Buddhism”为主题的文章,其作者包括阿兰?瓦兹,杰克?科鲁亚克,盖瑞?斯奈德和铃木大拙,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除文学领域外,铃木大拙的禅学思想还受到了大批西方心理学家的欢迎,如埃里希?弗罗姆、卡伦?霍尼和卡尔?荣格。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日本禅学大师抵达美国传教,建立了较大的禅学中心,吸引着普通民众前来参禅打坐。“Zen”开始渗透美国社会不同阶层。这些来自日本的学者和禅师普遍都与美国受众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而更加促进了其所传递信息的接受。以铃木大拙为例,“铃木大拙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个人魅力有关。正如之前所说的,他从来不会冷落任何一个听众。所以,大多数对铃木作品的判断都会受到评判者对其个人印象的影响”[15]。
这种日本学者和僧人与美国受众之间的亲密接触,再加上特殊时代背景下有关中国禅的原始信息的缺乏,导致日本学者和僧人的观点没有受到任何质疑,几乎被全盘接受。在西方受众心中,“Zen”就是“禅”,是世界上仅存的禅、唯一的禅,是日本文化所特有的精神。中国禅(Chan/Ch’an)虽然有时也被提起,但大都是作为日本禅的早期背景。例如,被称为“垮掉禅之父”的美国学者德怀特?戈达德,在其所编撰的《佛教圣经》(A Buddhist Bible)第一版中就写道,“这本书的目的是讲述早期印度佛教经过改造,并在六祖(惠能)时基本固定的过程。这本书的主体是禅宗(the Zen Sect)重要文献的英译”[16]。
值得一提的是,在来自日语的“Zen”在英语世界中大行其道的时候,中、越、韩学者对这一指称体现了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认同。1932年,中国学者胡适[17]发表了一篇题为Development of Zen Buddhism in China的文章,其中就使用了“Zen”而不是“Ch’an”①,尽管基于汉语拼音的“Ch’an”在之前西方传教士有关中国佛教的著作中已经出现过,如艾约瑟 1880年出版的《中国的佛教》[18] 。1959年,中国佛学家张澄基在纽约出版《禅道修习》一书。作者声称,该书内容完全基于汉语文本,目的在于系统地为西方读者介绍、分析和解释禅修,纠正西方读者对禅的误解和偏见[19]。但正如该书的题目所显示的那样,整本书中“Zen”都被用来指称中国禅。
20世纪60年代在欧美十分活跃的越南禅学大师释一行也主动使用“Zen”来指称越南禅。释一行的著作《越南佛教和禅宗》,第一次向西方读者介绍了禅在越南的历史、修行方法,以及禅对越南人民生活和文化的影响[20]。同样,20世纪70年代到达美国传教的韩国禅学大师崇山行愿,在其讲座和著作中无一例外使用“Zen”,而非“S?n”,来指称韩国禅,并自称为一个“Zen master”[21] 。
至此,“Zen”完成了其由中国禅的日本分支,到“独立、纯粹的”日本禅,再到涵盖所有禅(中国禅Chan,越南禅Thiên,韩国禅S?n)的语义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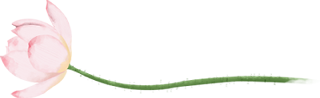
三、“Chan”的使用:“早期禅”“中国禅”和“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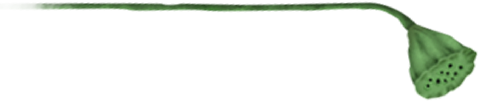
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佛教学者开始对其之前从日本学者那里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反思。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也开始有机会得到有关中国禅的第一手资料。早期日本学者对禅宗历史的歪曲及其写作背后的民族主义情节逐渐受到揭发和批判。与此同时,中国佛教大师开始进入美国传教,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用英文写作。“Chan”(Ch’an)的使用逐渐增多,打破了长期以来英语中只用“Zen”来指称“禅”的局面。
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禅的中国起源和真实历史。1967年杨波斯基敦煌本《六祖坛经》英译本中对于8世纪中国禅(Ch’an)的详细研究拉开了早期禅研究的序幕,“Chan”(Ch’an) 在英语中的使用逐渐增多[22]。但值得注意的是,“Chan”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作为唐、宋、元时期,即13世纪之前中国禅的指称。受之前日本学者的影响,许多学者仍认为,禅在现代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例如,华裔学者张钟元在其1969年出版的《禅的原始教义》中就写道,“13世纪起,禅在中国消失。日本僧人和学者继承了这一传统。一些已经在中国消失了的禅学文本在京都和日本其他地方的寺庙中得以保存。作为一名来自中国的禅门学子,我向维护了禅学教义、并帮助当今世人了解这一传统的日本僧人和学者表示感谢”[23]。所以,在张钟元的笔下,“Ch’an”仅仅指称13世纪之前的中国禅。
但中国禅在13世纪之后,即传入日本之后,就立刻消亡的观点,并非没有受到质疑。早在1967年,美国佛教学者尉迟酣就明确指出:“一些读者可能听说过如下言论,禅(Ch’an)仅在日本存活,中国禅很早以前就死于迷信和腐败。1934年,铃木大拙在一次中国佛教实地考察之后,曾声称,‘我们对中国禅已不复存在这一现象深感痛心’。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在许多寺庙中,成千上百的中国僧人仍在大师的指导下严格进行打坐参禅,至少持续到1949年。”[24]
20多年后,尉迟酣的研究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赞同。20世纪90年代起,布赖恩?维多利亚和罗伯特?沙夫等学者开始对禅的西传过程中所掺杂的日本民族主义进行批判。与尉迟酣一样,沙夫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学者笔下中国禅已经消亡的观点是对事实的故意歪曲。“我们[在铃木大拙的书中]读到,中国佛教在13世纪之后,也就是日本刚刚接触到禅之后,马上就停止发展了……实际上,直到当代,佛教仍在中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25]。当今禅学仅在日本这一口号背后,是民族主义思想在作祟。在日本学者看来,“既然亚洲精神的根基在于禅,而纯粹的禅只在日本得以存活,日本就有权利,甚至有义务,担任亚洲各国的领导者,带领贫困的亚洲兄弟前进”。在沙夫的文章中,“Ch’an”被用来指称中国禅,而“Zen”则被用来指日本学者笔下的日本禅。这一用法在学术界也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然而,“Zen”在英语世界中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使用使得许多 西方学者仍习惯于将其作为“禅”的统称。美国学者莫腾?舒特以研究中国佛教闻名,在其2008年的著作《禅如何成为禅》中,舒特就其术语的选择做了说明,“本书中,为大家熟知的日本术语‘Zen’用来统称以中国禅为源头的东亚各个佛教流派的教义、思想和文献。在具体讨论中国禅、日本禅和韩国禅时,我将分别使用‘Chan’‘Zen’和‘Son’”[26]。2017年,史蒂芬?海恩在其著作中采用了同样的策略。“Zen在本书中除用来指称日本的禅学运动和发展之外,还被用来指称整个宗教传统[禅]。‘Chan’指中国所特有的与禅相关的人、地区和事件”[27]。 在学术界之外,“Chan”的使用更为广泛,不仅用来指称中国禅,甚至也逐渐开始作为禅的统称。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僧人相继抵达美国进行传法,招收美国弟子、成立佛教机构并出版著作,如宣化上人、圣严法师、星云大师等。这些僧人大都同时教授弟子用汉语诵读经典,推动了“Chan”在普通民众之间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这些中国禅师的作品中,“Chan”经常作为禅的统称,但“Zen”并未完全消失。以著作等身的圣严法师为例, 其作品标题中大都使用了基于汉语拼音的“Ch’an”,如1987年《心的诗倡一一信心铭讲录》(Faith in Mind:A Guide to Ch’an Practice),1996年的《法鼓:禅之生活与内心》(Dharma Drum: The Life & Heart of Ch'an Practice);但也偶尔出现日语的“Zen”,如2002年的《禅的智慧》(Zen Wisdom)。
需要承认的是,整体而言,“Chan”在英语中的使用仍没有“Zen”那么广泛。许多学术性不强的著作,也许是受到编辑或者出版社的影响,不仅使用“Zen”作为禅的统称,甚至倾向于把中国禅简单称为“Zen”或者“Chinese Zen”。许多中国学者的著作也被英译者冠以“Zen”或“Chinese Zen”的标题。如南怀瑾的《禅与道概论》之“禅的部分”被翻译为Story of Chinese Zen,吴言生的《中国禅——一条通向宁静与幸福之路》被翻译为Chinese Zen: A Path to Peace and Happin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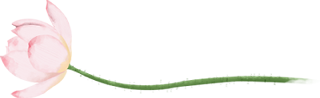
四、“Zen” “Chan”之争对维护文化话语权的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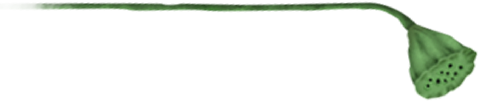
“Zen” “Chan”之争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文化的话语权不仅需要该文化成员有意识的建立和维护,有时还需要与其他文化进行竞争,以获取属于自己的发言权。由于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在汉文化圈的巨大影响,以及近代中国所经历的特殊历史,类似“Zen”对“Chan”文化话语权的争夺并非特例。因此,在扩大中华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增强中国文化话语权的过程中,我们要坚守阵地,有意识地建立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Zen”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名称背后,是日本民族主义对中华禅文化的否认与抹杀。由于“Zen”与日本文化的密切联系,可以想象,使用“Zen”这样一个名称不仅不会对中国禅文化对外传播做出任何贡献,反而会强化西方受众多年来的错误印象,使传播效果与我们的预期背道而驰。
正如之前学者所指出的:“传统文化的国际认同薄弱约束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塑造。要想跨越国际认同的障碍,增强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必须扩大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对话,为提升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认知创造机会,为塑造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认同提供平台。”[29]要想获得国际认同,就必须拥有文化自信,努力摆脱其他文化强加的指称和言说方式,用我们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术语,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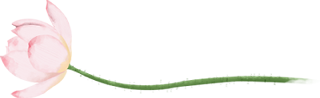
五、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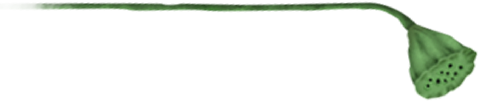
本文回顾了19世纪末以来“Zen”在英语世界中的传播和语义演变,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Chan”的崛起。尽管整体而言,目前英语世界中“Chan”的使用仍不及“Zen”那么广泛,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Chan”已经在逐渐走出日本“Zen”的阴影,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普通读者所接受。正如华裔学者王友如所指出的那样“在过去20年间,在许多影响较大的领域中,以英语出版的有关禅[Chan]的学术著作大大超过了有关日本Zen的学术著作”[30]。这一成就与大量中国学者和僧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反观国内,以知网论文检索为例,汉语撰写的论文英文标题与摘要中,“Zen”的出现频率远远高于“Chan”。显而易见,相当一部分国内学者只是简单地将”Zen”作为“禅”的英文翻译。考虑到“Zen”西传过程中所体现的日本民族主义情节和当今中华文化话语权的重要性,本文对这部分学者的做法提出质疑。毫无疑问,基于汉语拼音的“Chan”应该,而且必须得到使用。只有这样,才能彰显我们的文化自信,由于历史原因被抢夺的禅文化话语权才有可能逐渐回到中国学者手中。
注释:
①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50年代,胡适公开批评铃木大拙禅学不讲历史,随后发表文章Ch’an (Zen) Buddhism in China: Its History and Method,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1953,3 (1):3-24,其标题中“Ch’an”的使用引人深思。
[参考文献]
[1] 谢清果.中国文化的话语权提升之道[J].人民论坛,2016(23): 10-14.
[2] 太虚.太虚大师全书[M]. 新竹: 印顺文教基金会, 2008.
[3] 蒋坚松.《坛经》与中国禅文化的国外传播——兼论典籍英译的一种策略[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4): 48-53.
[4] Speake, J. and M. LaFlaur. The Oxford essential dictionary of foreign terms in English[M]. Oxford: Oxford Universtiy Press, 1999.
[5] 高洪. 明治时代的日本佛教改革运动[J]. 日本研究, 1996(3): 75-83.
[6] 葛兆光, 怎样面对新世界?——1893年芝加哥万国宗教大会后的中日佛教[M]//蒋坚永, 徐以骅. 中国宗教走出去战略论集.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5.
[7] Suzuki, D.T. The training of the Zen Buddhist monk[M]. New York: University Books, 1965.
[8] Fader, L.A. Zen in the West: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1893 Chicago 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s[J]. The Eastern Buddhist, 1982, 15(1): 122-145.
[9] Seager, R.H. The dawn of religious pluralism: Voices from the 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s, 1893[M]. Chicago: Open Court Publishing, 1993.
[10] Sharf, R.H. The zen of Japanese nationalism[J]. History of Religions, 1993. 33(1): 1-43.
[11] Suzuki, D.T., The Zen Sect of Buddhism[J]. 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 1906: 8-43.
[12] Nukariya, K. The religion of the samurai: a study of zen philosophy and discipline in China and Japan[M]. London: Luzac, 1913.
[13] Suzuki, D.T. Japanese Spirituality[M]. Kyoto: 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1972.
[14] Suzuki, D.T. and R.M. Jaffe. Zen and Japanese cultur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15] Faure, B. Chan insights and oversights: An epistem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Chan tradition[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6] Goddard, D. A Buddhist Bible[M]. Vermont: Cosimo Classics, 1932.
[17] Hu, S. Development of Zen Buddhism in China[J].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Review, 1932, 15(4): 475-505.
[18] Edkins, J. Chinese Buddhism: a volume of sketches, historical, descriptive and critical[M]. London: Trubner & Company, 1880.
[19] Chang, C.-C. Foreword[M]//C.-C. Chang. The practice of Zen. Harper & Brothers: New York, 1959, ix-xi.
[20] Thien-An, T. Buddhism and Zen in Vietnam in Rel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Asia[M]. Los Angeles: College of Oriental Studies, 1975.
[21] Sahn, S. Only Don’t Know: The Teaching Letters of Zen Master Seung Sahn[M]. San Francisco: Four Seasons Foundation, 1982.
[22] McRae, J.R. The Northern School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an Buddhism[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6.
[23] Chung-Yuan, C. Introduction[M]//C. Chung-Yuan. Original Teachings of Ch'an Buddhism. Vintage Books: New York, 1969, vii-xvi.
[24] Welch, H.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Buddhism, 1900-1950[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25] Victoria, B. Zen at War[M]. New York: Weatherhill, 1997.
[26] Schlütter, M. How Zen became Zen: The dispute over enlighten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Chan Buddhism in Song-Dynasty China[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27] Heine, S. From Chinese Chan to Japanese Zen: A Remarkable Century of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28] Yen, S. Zen Wisdom: Conversations on Buddhism[M]. Berkeley: North Atlantic Books, 2002.
[29] 赵庆寺. 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路径[J]. 探索, 2017(6): 114-121.
[30] Wang, Y. Preface[M]//Y. Wang.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Chan Buddhis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Lanham, 2017:xiii-x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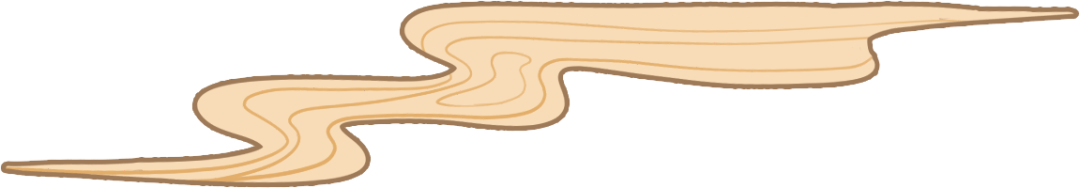
识别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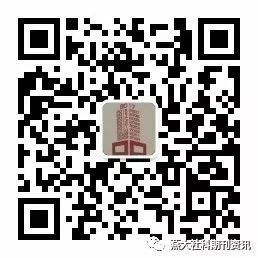

关注我们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投稿网址:http://xbskb.ysu.edu.cn
编辑部联系电话:0335-8047985

投稿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