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樟柯:各位观众,下午好。谢谢大家来到平遥国际电影展,今天特别冷,我要代表平遥的天气向大家表示抱歉。
这场是选片人论坛,今天平遥国际电影展来了很多友好的、其他影展的艺术总监和节目策划,借这样一个机会,我们想让这些选片人、节目策划与艺术总监坐下来,交流关于亚洲电影和中国电影的信息,传达来自他们角度的一些观察。
因为每位选片人每年都要接触并观看大量的中国电影或是亚洲电影,通过这些资深的节目策划与艺术总监的眼光,来看这几年亚洲电影、中国电影有什么样的特点,我想今天的这个论坛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那么我首先要介绍萨布丽娜·巴拉切蒂(Sabrina Baraccetti),她是来自远东国际电影节的节目策划。
远东电影节是欧洲最大的介绍亚洲电影的电影节,每年开春在意大利东北部的小城乌迪内举行。咱们耳熟能详的导演,像杜琪峰导演、冯小刚导演,都曾经在远东国际电影节获奖;这个电影节专注于展映来自远东地区的优秀影片。欢迎萨布丽娜·巴拉切蒂。

我还要介绍卡洛·沙特里安(Carlo Chatrian),他从2013年起担任洛迦诺电影节的艺术总监。
洛迦诺电影节是一个专注于发掘全球年轻导演作品的电影节,我们的马可(指马可·穆勒)过去工作了十几年,卡洛工作了十年。今年开始卡洛·沙特里安就是柏林国际电影节的艺术总监了,这一次他也担任我们平遥国际电影展费穆荣誉的评审,我们有请卡洛·沙特里安。

第三位是克里斯蒂·琼(Christian Jeune),他是戛纳国际电影节的选片总监,为戛纳电影节工作已经超过三十年,几乎每年这个季节他都会来到亚洲,来到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来看最新的影片。我相信他看的中国电影比我还要多,所以我们有请克里斯蒂·琼。

我们现在欢迎基里尔·拉兹洛夫(Kirill Razlogov),他是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总监,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是世界上历史第二悠久的电影节,仅次于威尼斯电影节,同时也是俄罗斯最大的国际电影节。

我们要介绍市山尚三(Shozo Ichiyama),他是东京银座电影节的主席,同时也是一位制片人,监制过侯孝贤导演的电影,也监制过我的《站台》。他的展映每年11月举办,很多中国电影在他的电影节上获过奖,我们有请市山尚三。

最后当然就是我们平遥国际电影展的艺术总监马可·穆勒,今天这个论坛是由马可·穆勒和我共同来主持。
马可·穆勒:我希望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还有几位非常重要的电影界代表也在场。他们的后面是戛纳国际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亚洲区的选片人本杰明·伊洛斯(Benjamin Illos ),以及洛迦诺电影节的中国地区选片玛丽亚·雷戈里(Maria Ruggieri)。
贾樟柯:我也再补充一下,我们会有一个“遇见选片人”的大派对,所有来自世界各国的选片人都会出席,并介绍他们自己负责的电影节展,欢迎大家晚上也参加那个派对。

关于“经典”电影节模式的反思
马可·穆勒:下面我会用英文来发言。这样咱们可以畅所欲言。
第一个问题是,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电影节,当然说起来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有很多的电影节还是在重复“原罪”。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是世界上第一个电影节,在它诞生的时候,也就是1932年,出现了这个“原罪”。
一开始大家都感觉电影节是一个很沉闷的活动,这也确实事出有因,因为当时是由酒店来设计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入住酒店的时间能长一些,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电影节有发展旅游的任务在身的。但是在平遥我们还是“安全”的。因为平遥的酒店全年都满客,即使平遥不办电影节,游客也会来平遥来旅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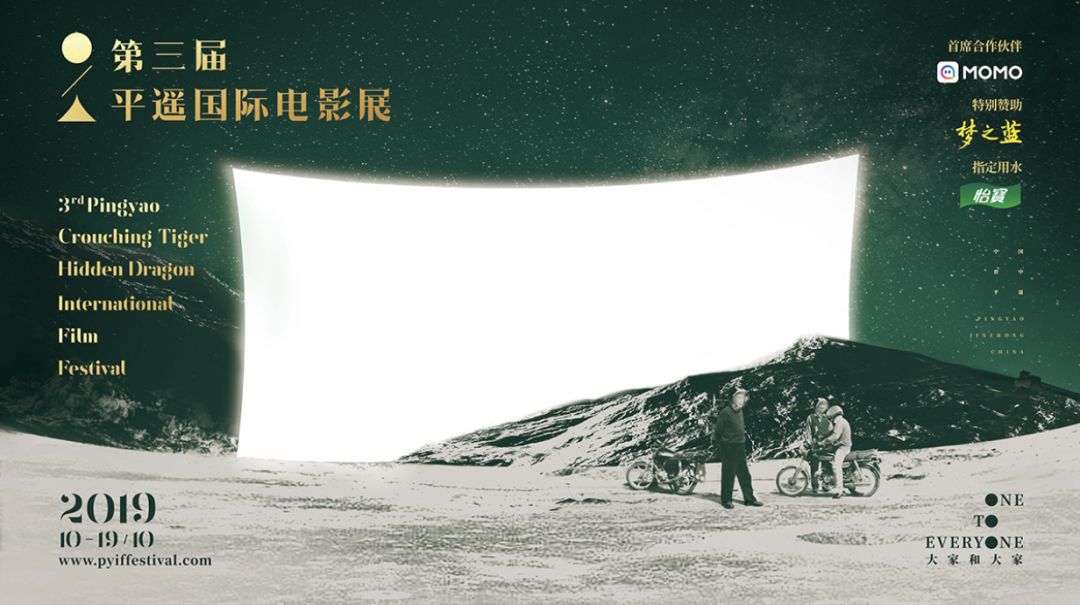
不过有了电影展之后,我们能吸引很多年轻学生,能够吸引到不同于普通游客的来访者。但是我们多数人,今天应该要反思一下电影节的活动,也就是一种所谓的“经典的”办展模式。
比如沙特里安刚刚在柏林电影节上为大家推出一个新单元,巴拉切蒂那边也推出了非竞赛类单元;即使在戛纳那边,也推出了新的、也就是所谓的电影基金单元,更多地关注于青年电影人;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也有点类似戛纳、柏林,甚至比威尼斯的规模还要大一些,在莫斯科那边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各种各样的电影都有,我还记得之前在博物馆里面也办了展映。
而市山尚三先生更是要去应对一个难题,正好你们的电影节就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之后,虽然说你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供职多年,但是你的电影节的需要,跟东京的需要有所区别。你觉得这种常规的办电影节的方式还可行吗?

市山尚三:就像刚才马可主席所讲,从1992年到1999年,我供职于东京国际电影节,之后我离开并创立了一个新的电影节。我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东京电影节是一个很大的电影节,就像上海国际电影节这样,有大量的电影首映——不只有艺术电影,同时也有很多商业片。
我们这个则可以说是另辟蹊径,展映的除了亚洲电影以外,很多是独立制作的电影,或者是艺术电影,并且我试图去选择当年最好的独立电影以及艺术电影。
尽管观众对我的选片还算很满意,但是多数的媒体报道还是只报道了大片或商业片——即是说我们展映的质量很高,但报道却很少,所以我们电影节名气不是很大。因此我们就设立了一些所谓的奖项,比如说最佳亚洲电影等等,通过奖项来提高知名度,但效果还不是特别显著。
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办了银座电影节,这是一个很小的电影节,跟平遥很像,可能比平遥还小一些,竞赛单元就十部,就是一些崭露头角的亚洲电影人的作品。还有一些特别的项目,展示一些有国家主题的东西,每一次也就是三四十部电影进行展映。我们的场地就只有一个,这个场地本身很好,我们只是在这一个地方进行展映,所有人都能在同一个地方相互见到。
这个很重要,因为东京电影节规模非常大,我去的时候一次就只能见一部分人,不可能在一个地方把所有人都见全了。但是在银座电影节,大家都在一个地方,如果我就坐在中庭那边,我基本上谁都能见着——这就是我们如何开始创办这样小而精的独立电影节的,因为东京电影节太大了,我们就办这种小的。

后来电影节进行了更名,同时也跟柏林国际电影节等等去合作,相当于我们是柏林的一个东亚版本,选出十五个年轻的电影人,他们可能来自东亚或者东南亚,然后我们办这么一周的活动,每个人都可以把他们的新作品带过来进行介绍,由专家来决定奖项。
至于最佳电影的项目,完全是东京市政府出资,十年以来办得都非常成功。《爸妈不在家》的导演陈哲艺,当时就在我们那边进行了展示;这次平遥国际电影展这位导演也带来了他的新作品。当时在还没有完片的时候,陈导演就把这个片子带到我们那里去看,所以我们一开始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然之前也有一些别的崭露头角的年轻电影人到我们那边去参加选片,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他们有的时候选择到我们那边去首映,而不是到东京电影节去首映,是因为我们希望以这样的一个平台来推介年轻的亚洲电影人,同时让他们的片子更容易被别的电影节选到。
不只是我的电影节,其他的电影节也都有这样发掘年轻电影人的单元,通过这种大师班或者作品研讨会等等的方式。柏林、戛纳那边也有,每一个电影节都有一个类似的特色单元,能够去发掘、帮助电影行业的新秀。在平遥国际电影展这边有平遥一角,也是去致力于挖掘、培养电影新人。
在九十年代的时候,电影虽然在电影节进行了首映,但观众想看到依然不容易;现在于电影节上首映之后,电影能够很快在网上被看到,或者人们可以在亚马逊上买DVD碟片看到。现在看电影方便了,电影节不仅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看电影的渠道,更多的是增加了一重使命。就是我们要向新电影、未来的电影做出贡献,这样能去打造新的一代电影人。

马可·穆勒:拉兹洛夫有一件事可以说让我印象深刻,我管他叫教授,是因为他特别强调培养新一代的电影导演、电影学生。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历史悠久,依然不忘初心,培养电影的新人新作。
基里尔·拉兹洛夫:现在的电影节活动非常多,而且现在商业宣发在全球也是越来越统一,也就是在全球每个院线,都是那25个片。而且现在故事片虽然拍了很多,但是大部分就只能在网上看到,在院线看不到。
所以莫斯科电影节也做了一些调整,以前就是在苏联阶段,那个时候内容审查严格,中国这边可能当时情况也比较像,大家看不到娱乐电影,要想看西方的这种有娱乐性质的好莱坞片子,也只能到莫斯科电影节去看,因此当时来看片的人非常多,比如说一个厅里坐两万人也不算太多。来自于苏联各地的人到莫斯科电影节就是为了看两个礼拜的电影。
当然了,现在就不是这样了,我们现在也展映一些大家在商业院线中看不到的电影,往往是一些艺术电影,或者是实验电影等等。也就是说我们的使命很不一样,但是我们所做的工作实际还是一样的,就是希望能够扩大受众面,能够让观众去看到不同类型的电影,跟别的电影节、跟别的院线不一样的电影。

我们不知道今后会怎么样,但是我不会为电影的未来感到过于担心,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电影在出现,而且年轻人会有办法去做出非常专业的表现,我们不用担心年轻人。所以对我们来说莫斯科电影节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应该注意到很多学生想要展现自己电影,这些学生就是明天的电影导演,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些年轻的苗子,不光是莫斯科的好苗子,我们还要从威尼斯,从戛纳吸取人才。
可能我们推出的电影并不是家喻户晓的大导演的,但是如果我们觉得它会引起异议,那也值得推出,哪怕是默默无闻的导演。商业大片竞赛片我们肯定也会放一些,但是我们会主要放映那些第一次推出、也就是处女作的电影。
比如说在俄罗斯的最北的地方——完全荒芜的一个地方,我们从那找到了一些电影导演拍的电影。那个地方很难进行拍摄,因为经常是零下50度;拍出的电影更别提在国际上有影响了。
所以我们把他们的电影带到莫斯科电影节上,这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就努力地说服他们,让他们把这个首映放在我们的电影节,而不是他们共和国自己的电影节上,这样会有更大的影响力;同时他们也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褒奖,对电影来说这个是特别好的事情。
虽然我们说这个电影导演是年轻人,但是对我来说,做电影的人都是年轻人,都是有一颗年轻的心,这就好像是法国电影新浪潮,但却发生在俄罗斯的极北苦寒之地。

马可·穆勒: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戛纳非常成功,电影市场也是蓬勃发展,所以每两三年都会面临新的挑战。作为几乎是每年的第一个重大的电影节,你是怎么面临日夜出新的挑战的呢?你怎么筛选片子,同时也做到不会让其他的电影工业受到重创?从六十年代开始,就有新的电影形式和电影评论方式出现。
比如说今年的《我们的母亲》——这部电影同时也在竞争平遥的罗西里尼荣誉——评论家的评价并不是那么好,但是却获得了金摄影机奖,你是怎么看待新电影、青年电影在戛纳电影节的分量的?

克里斯蒂·琼:首先戛纳是一个很特别的电影节,它没有真正的观众,不像一个一般的电影节可以买票观影等等,它只为专业人士举办,这是它的特点。但是回到你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电影节如何面临挑战。
对我们来说电影节的目的是保留我们的电影,如果我们提供的选片非常好,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哪怕现在的观众可以在网上下载一些电影,在各个渠道都能够获得电影。比如说里昂最新创办的这个卢米埃尔电影节,里昂的观众可以说是蜂拥着去观看最新的电影,尤其是年轻的观众,真的是冲进电影院去看新的釜山电影节刚刚出来的电影。这是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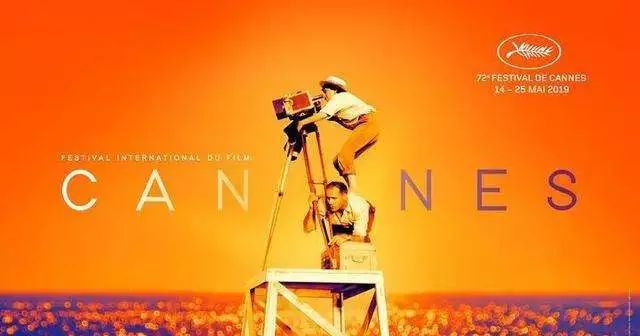
另一点我想说,电影工业可以说是一个很脆弱的工业,但是它也有强大的力量,就是把大家凝聚在一起,而电影节恰恰是一个这样的很好的凝聚的平台,平遥就是很好的一个证明。还有就是里昂,里昂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光是整个城市都被电影节带动起来,周围郊区也是一样。
所以我一方面对世界是很消极的、很悲观的一个人,但是对电影节还是保持足够的乐观,我觉得未来我们肯定需要大量的支持和帮助,电影节不可能独自去承受整个电影工业的重担,电影节永远是一场持续的斗争——不管是威尼斯,还是柏林,还是其他的电影节,都是一种永远不断的战斗。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孟买电影节,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孟买电影节能够给当地观众带来官方不会放映的电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回到你的问题,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就是把电影带给观众,并且选好片;选好片就是有一些人坐在一起去思考什么样的电影应该在这个时候带给观众。我觉得还是有点乐观的吧。

电影节与观众
马可·穆勒:沙特里安是在一个很大的城市、在柏林电影节做艺术总监。像平遥,像法国的蓝色海岸,戛纳,还是比较小的城市,但是柏林那么大;让人们去一个城市的电影院看电影,尤其是这么大的一个城市,人们都很繁忙,如何把观众吸引到电影院呢?我们重点讲柏林,因为我们觉得你把柏林电影节更加简化了,整理了新的单元。
卡洛·沙特里安:可能对于我来说,柏林电影节才是刚刚开始。我想从头说,马克·穆勒先生您说过,电影节最开始是一个很沉闷的东西。
我是三十多岁的时候开始做电影节的,对我来说首先电影节是一个人们聚集的地方,在电影节里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对于我这样一个选片人来说就是要创造这么一个空间,让所有的人能够共居共生,并且丰富滋养这样一个空间,所以选片对我来说就好象是放不同的石头,让大家看到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路径。我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如何创造这么一个空间,在这么大的一个城市让人们共生,尤其是在柏林。

柏林电影节是非常成功的,一百万的观众会去看,我的目的、我的挑战就是让他们来的时候感到有意义——首先不是给他们发号施令说你看什么,你不看什么,而是让他们来的时候感到没有白来,很有意义。创造一个新的单元,是因为我们知道创作电影、制作电影都是不断进化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
过去可能柏林缺少某种类型的影片,但在平遥国际电影展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可能看起来有点脆弱,没有大导演或者是著名的名字,但是很有意义的这么一种电影,所以我把这种想法融合进来,创造了一个新的单元,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当然我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回答,因为柏林电影节是一个太大的话题。

马可·穆勒:因为玛丽亚是洛迦诺的中国地区选片总监,我想我们三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你刚才提到共居共生。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所有中国学生,都明白洛加诺可以让八千个观众在一个电影厅里去看一部片子,这种体验真的是世所罕有的——我们和八千个人同呼吸、共命运,体验同样的感情。
这是非常独特的体验,也是一个对发行来说非常好的案例。这也是让我在平遥非常遗憾的一点,可能我们的电影还不能证明自己的市场价值。虽然我们的艺术价值已经很高了。所以你能不能在这一点上谈一谈?
卡洛·沙特里安:你知道洛迦诺确实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一边是湖,一边是山,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中间就这么一小块地,所以你很容易聚集起来一堆人。
电影节不光是一个看电影的地方,同时还是一个见人的地方,我们可以去跟别人相见,可以去讨论,可以去交流,比如说像戛纳、洛迦诺这些地方都是能够去创造一个我们共同体的空间,在柏林也有这样一个空间。柏林电影节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要采取的策略也应当是完全不同的。
洛迦诺那边,我想您肯定比我更熟悉它的特点是什么,可以说在这十天当中,大家住在一起。平遥也是这样,就是在这么一个古城当中,而且是在围墙之内,从心理上来说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围在一起的感觉。这是我的体会。

马可·穆勒:讲到共同体的感觉,我就想说远东国际电影节的选片。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一个观众群——观众群其实是一个抽象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里面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大家看完电影的反应都不一样;不一样的观众群就意味着我们把人聚在一起,他们的教育背景不一样,观影的习惯也不同。
我们要把大家聚在一起,大家在同样的地方让感情去碰撞。可能会是早上九点有1500人,他们对电影的反应都是非常与众不同的,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共同的观影体验。电影节的演变发展也得益于观众的活跃度。
萨布丽娜·巴拉切蒂:其实我们电影节的反应取决于我们观众的反应,确实,我们在乌迪内这样的一个小镇,离威尼斯不远。我们在21年以前创办这个电影节,马可主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创办我们的电影节的时候,我们尽力去做一些我们有特色的事情,当时我们是从香港开始起步的,我们对香港电影非常热爱,我们想把香港的电影人,导演、演员请到我们那边去,跟我们见面。那时候我们还是充满热情的年轻人,我们有自己的电影观。

之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在那个时候,或者在现在,我们会考虑观众的选择。大家来到一个影院观影,他们可以投票,然后选择他们自己最钟爱的电影是什么,这样可以说选片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活动。也就是我想看一个电影的话,要跟其他的一千个人一起共享时间感情;选片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步骤,而且你可以表达对电影肯定,或者是保留意见,所有的这些反应都可以在影院内做出。
让电影上映,然后去反馈,这就是我们电影节的灵魂,从九点一直要演到半夜,大概一天会有八到九场。我们知道大家看电影的渠道是很丰富的——除了电影节之外,在互联网上也可以看到,但是在电影节上有更多这种集体的感觉,像乌迪内这样小的电影节也是能够为大家营造这种集体的感觉的——大家一年一度来到我们这边看看有什么样的新片,在世界的另外一端有哪些发展新趋势。
但是有一些电影,想让我们通过其了解中国的发展变化,还是挺难以理解的。当然不同电影节的选片各有侧重,我们这边选的商业片会多一些,不只是选艺术电影。这就是我们可能给到大家的一种不同的选择,也是我们二十年来的一种特色。

电影节与市场
马可·穆勒:你继续拿着麦克风,我还要再追问第二个问题,然后再开放提问。
你刚刚讲到有市场的影响。电影节不应该是,比如说市场不行的,我们电影节接过来,好像是代位的角色。可能电影节更多的是强调跟市场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取向。比如说中国电影,什么样的中国电影能够在电影节上更有前景,我们就能够做那些工作,可能在本地搞一些首映,来更好地推介中国电影。因为中国电影数量大,同时又非常多样。另外像俄罗斯那边也是这样,俄罗斯电影也是数量大,种类又多。
萨布丽娜·巴拉切蒂:可能有一些中国电影是平常关注度不够的。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希望能够对中国做更深入的研究,从而能够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从二十年前就试图去了解中国电影,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比如冯小刚的电影。
冯导跟我们也是颇有渊源,他的电影在欧洲首次上映就是在我们那边,他更多拍的是商业片,电影节的重要意义也是在这个方面能够得到体现,我们希望能够深挖,能够给观众们去呈现他们平常看不到的一些电影,比如中国电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国的电影界可以说在经历革命,一开始只有两千块屏幕,现在超过六万个银幕,这个银幕数量可以说是一个飙升。而且我们可以介绍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这个市场的发展过程当中商业片也有一个迅猛的发展。

马可·穆勒:沙特里安,你在洛加诺那边就接触过中国电影,你觉得在柏林电影节,中国电影的未来如何?柏林电影节有相关的一个论坛支持电影界的新秀,让他们能够为人所知,为人所见——创造条件让新人新作得到承认,比如贾樟柯的《小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同时你们应该也播大片,我还记得张艺谋就讲到,《英雄》这个大片就是在柏林首映的。
卡洛·沙特里安:洛加诺也好,柏林也好,都是很成功的电影节,我们跟中国电影的关系也都非常成功。在洛加诺那边,可以说,您帮我们打开了很多大门。在我供职时期也是展映了一些中国电影,同时又有一些中国电影获奖。我记得有两部得到了金熊奖,也就是说柏林电影节跟中国的电影渊源更长,维度更多——有一些是艺术电影,甚至是官方没有完全批准的电影,同时也有一些成熟电影人的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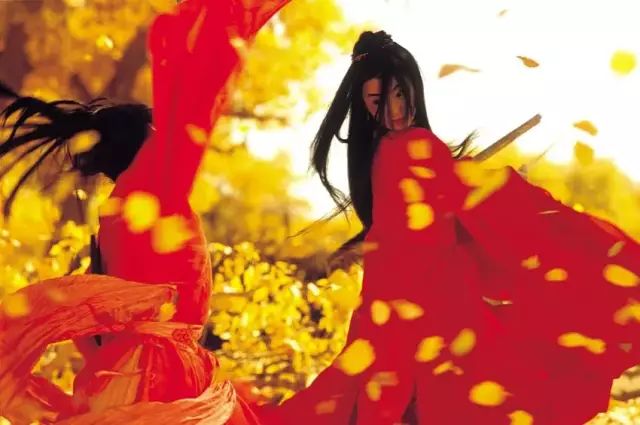
柏林很有独特性,不管内容也好,还是观众也好,都是我还需要再进一步去了解的。对我来讲电影就是一种旅行的方式,我更年轻的时候旅行得并不多,但是看电影可以带我到世界各地。现在在柏林这一点还是能够实现的,我们急不可耐地要去看到来自各国的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
中国电影深植于现实,能够通过看中国电影来感受中国的现实,现实感非常强烈,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电影在柏林如此之成功的原因之一。同时还有一个障碍就是语言,我跟电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首先我要相信电影的内容,然后我要去用电影的方式去应对这样的内容。
中国电影就很有意思,因为中国电影非常多元,内容的张力很强,同时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声音,可能不为人所知,我们希望进一步去发现。我到平遥也是来进一步发现的,甚至像影探一样发现更多能够介绍到柏林的电影。

马可·穆勒:在威尼斯这边,有很多的金狮奖后来颁给中国,可能比金棕榈奖要多一些。因为戛纳那边面对的是全球市场,戛纳往往就是市场趋势的一个起点,使得中国电影能够从戛纳走向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变化会发生呢?
我给大家举个具体的例子吧,戛纳对于电影来说一方面有很大的作用,同时又带来了很大困难。比如说《霸王别姬》这个电影得了金棕榈奖,使得那个时候中国电影的价格飙升,已经超过了市场的承受力,结果有那么两三年谁也不敢碰中国电影以及华语片,因为价钱太高,买不起,宣发不起。就这个方面我们如何去解读市场?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解读市场。

克里斯蒂·琼:戛纳之所以成功,可能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法国电影业非常发达,宣发的体系也很健全,当然电影之间有很多竞争,电影业的从业机构有很多竞争,有时候会把价格抬上去。
其实不只是中国电影,可能获得金棕榈奖的有很多都是这样——韩国电影,比如说《寄生虫》,我觉得我们没有关注特别的某个国家。其实说来说去,什么会发生的就会发生吧。如果中国电影很成功,当然是非常好,但不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能预料到的。

马可·穆勒:我想说的其实是,我不明白作为市场运营为什么对法国市场和北美市场的信任度不一样。举个例子,贾樟柯的《三峡好人》,这个《三峡好人》的票房是一百万。
贾樟柯:对这些数字我不是太关心,我没有概念。
马可·穆勒:我记得是这个数字,我觉得这个数字挺惊人的,你都得了威尼斯金熊奖了,比意大利的票房还多六倍。我的意思是说欧洲的发行和北美,尤其是多伦多的发行,区别这么大,作为戛纳这么大的电影节是能够推动市场趋势的,也能够影响市场。

克里斯蒂·琼:我们也不是主动地去推市场往哪个方向走,我觉得没有电影节能控制市场吧。当然在戛纳媒体是非常大的一个群体,五千个媒体工作者,可以说是一个媒体的大聚会——不管是好是坏,总之是一个非常大的聚会。可能是因为电影工业很蓬勃,然后媒体工作者很多,所以我们的影响力很大。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很多作者,他们会得到金棕榈奖,但是他们的上座率也没有多高,可能最好的电影也只有八千这样的上座率。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很简单,就是我们做我们的工作,然后之后我们就顺其自然,没有任何的计划和预估去制造某个市场的趋势,没有。

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节
马可·穆勒:基里尔·拉兹洛夫先生,今年在你们的电影节里有很多中国电影,有不同的单元,你是如何解读在莫斯科电影节中的中国电影的呢?但是这个成功却不能在俄罗斯其他的电影市场上被复制。
基里尔·拉兹洛夫:中俄两国电影关系和发行的关系源远流长,我们一言两语说不完,可能从五十年代开始,当时的苏联就大力地支持中国的电影发展,很多中国人都去了俄罗斯,去学电影。现在中国电影经历了很多的复兴,我们都很开心。俄罗斯也在经历巨大的变动,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经典中国电影,比如说《三峡好人》。
在俄罗斯大量地展映中国电影的趋势停止了,但是我们还在展映韩国电影。怎么解读呢?我们的感觉是,可能我们中俄两国的交流越来越多,大概三四次交流会展映三四十部电影。
我们的莫斯科电影节,有一部很小的电影《塬上》,小预算电影,但是评审团非常喜欢,我对中国电影有什么看法,就是你很少能够在一些地方看到新的真正的中国电影!平遥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我们能看到新的电影,其实是在中国第一次能够看到没有出名的那些电影。
还有一些比较大的片子,在中国也有放映,我们也会做回顾展,来给大家看一下中国电影的历史是什么样的。我们做了好几次回顾展,我们以后还会继续做。

关于中国的新电影,我们的问题就是没有人见过,在这边都很难见到,所以更别提怎么带到莫斯科了。还有一点,就是我想说当我们提中国新电影的时候其实有不同的类型,有官方的,尤其电影节会重大推出的那种,传统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等等题材的。
很多俄罗斯观众很喜欢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种电影,因为他们也有一种怀旧的情绪。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在戛纳在其他的电影节比如洛加诺电影节大放异彩的电影。

马可·穆勒:市山尚三先生,我们的创办人贾樟柯先生已经说过了,《站台》开始市山尚三先生就一直和中国新电影关系是非常的千丝万缕。今后会如何继续支持中国新电影?
市山尚三:在日本,我们可能比别人更有机会看到中国新电影,为什么呢?哪怕是八十年代末,我们就已经能看到很多好电影了,因为我们有很多正规的发行渠道能够让我们获得这些电影。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很多老人喜欢看中国电影,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这样的电影特别有市场,有观众缘。但是关于年轻人的新的电影很难打入我们的市场。
2000年我开始做电影节的时候我曾经努力推过一些像《小武》这样的电影,我觉得2000年是一个很好的年份,娄烨导演的《苏州河》当时在日本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在特别放映中看到了这部电影,很多日本人都非常喜欢这部电影。2000年之后,宁浩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也获得了最佳影片,这是一个很小预算的电影。而且还有很多中国的网络电影拍摄者也会来展示自己的电影。

但其实我们在日本很难看到所谓的地下电影——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是官方审查制度允许的电影——那些电影确实很难找到合适的发行渠道、发行商。但是有这么几个特例,比如去年《大象席地而坐》,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电影,但很难在日本找到发行渠道。
但是放映之后有一个日本电影公司就购买了发行权。他们经常去柏林电影节,这个电影很长,是四个小时,所以他们也犹豫再三要不要买这个电影发行权。
但是这个电影公司有一个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他就一直力劝他的老板说买吧;他非常喜欢这个电影,他看了很多遍。所以有很多小的发行商他们去不了戛纳,去不了柏林,他们就在东京看。可能这是一个很小的我个人的努力,但是我一直都在尽全力来推动中国的新电影。

贾樟柯:刚才大家都聊了关于电影节,关于中国电影,我想在平遥有非常多的年轻导演,他们刚刚拍出了他们的电影,他们也非常关心影评人对于最近这两三年的中国电影,对于年轻导演的作品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有怎么样的种印象。这个印象可能包括好的方面,也有需要去进步的地方。我想请市山尚三先讲。
市山尚三:这个很难回答,每次我们找电影的时候,报名的中国电影很多,有时候我们觉得这部电影很好,但是有点像贾导或者娄烨这些别的中国导演的作品——有点相似。问题不在电影上,如果说我认为这个电影跟别的电影相似,一般我就不会去选了;如果说这个电影很不同于其他的中国电影,即使说他的质量没有那么好,那我还是会选过去参加我们的电影节。忠于你的内心,就按你的想法去拍,不要模仿别人的电影。这也算我的一个小建议吧。
基里尔·拉兹洛夫:我这没有什么建议,因为选片有的时候是随机的,我记得原来选过一个中国的电影,《月蚀》,是因为我在俄罗斯大使馆见了一个人,他有个中国朋友,他说这有一个青年导演拍了一个片子,然后我就把他选过去,很成功。我在鹿特丹看过《苏州河》,而且还是未成片的版本,我甚至说比成了片的还好。而且商业上也挺好,因为那边的宣发也比较成功。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中国电影让我惊艳,有一部叫做《俄罗斯的民歌》,讲到的是在中国的北方,尤其是东北,大家喜欢俄罗斯或者苏联的民歌。还有让我觉得惊艳的,是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中国电影——呈现了中国的社会问题。我想给青年的电影人的建议就是不要去跟从他人,就是去拍出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电影就好。

克里斯蒂·琼:我也想说同样的内容,我们没有必要给大家建议,电影拍好以后我们会去追着电影走,就像教授所讲到的,我们希望被惊到,被感动到,甚至心里起波澜,拍电影是你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追着你们。
卡洛·沙特里安:如果说我能给个建议的话:什么叫做被惊到,因为我们在周边都是电影,都是画面,我觉得有的时候缺乏更有思考的、能够更多地去运用声音来讲故事的电影,因为画面已经足够丰富了。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缺乏的,现在拍摄比较简单,有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拍,而是要等到那个合适的时刻到来,有的时候你不拍的可能比你拍出来的还重要。也就不只是说画面之外的这些东西,而是说你想拍没有拍的东西。前面这个我们说前面讲得很好,不要去模仿别人,你去模仿可能对你不利,因为你去模仿那样的东西就不是你自己的东西,那是模仿的作品。
萨布丽娜·巴拉切蒂:前面大家讲得那么好,我想再讲点别的也很难,我能讲的是什么呢?我想讲的是说去年咱们选了三部中国电影,从平遥这边选去,然后到乌迪内去展映。有一些我们觉得是处女作的作品,非常有意思,今年我想我们也会选的。
我想跟中国的导演们讲的,就是他们可能画外音用得太多,他们有时候会交代故事背景,这个可能在商业片当中比较常用,但是艺术片里并不是太多,有时候交代故事背景没必要。其实你不交代前因,也许艺术效果会更强烈一些,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技术问题,我想说一下。

马可·穆勒:有请另外一位来自戛纳的本杰明·伊洛斯也说一下,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电影有非常多的理解,包括戛纳那边,还有美国的电影节,也是对于中国很了解,应该每年都会来中国选片。我可以分享一个我的个人经验。我在威尼斯电影节的时候建立了一个威尼斯选片委员会,有一个重要的片子——后来戛纳那边还播映过修复版——当时他们虽然恨那个片子,但是还是选了那个片子,有的时候你即使说特别爱一个片子,也还是要经过选片委员会的过滤才行。
本杰明·伊洛斯: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首先从戛纳“导演双周”展角度来讲,我们选片的时候会考虑在比如大的电影节的边缘试探,我们跟我们所共事的人去交流,我们看到有意思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分享。近年来如章明的《冥王星时刻》,像这样的片子我们会介绍给别人,让这种有一些边缘化的电影能够通过电影节重新进入到大家的视野,让他登上更大的舞台。

马可·穆勒:玛丽亚,我希望没有透露你的秘密。你把很多的中国电影推荐给选片委员会,后来有一部被选中的,那是什么?
玛丽亚·雷戈里:我看了很多电影,各种各样的中国电影我都看过,有很多的新的主题,新的想法,新的风格。但是选片委员会,他们在办电影节的时候可以说非常忙,因为他们看的是全世界的片子,所以说我希望能够让他们了解中国电影什么地方是与众不同的,哪些是新的,比如他们可能重点就推荐两三部片子,我理解他们觉得中国无非就是很多个国家当中的一个,我当时看了很多很有意思的片子,可能中选的也就一两个,要做更多的工作。
至于描述说这个片子到底有什么地方有亮点,会使他们卓尔不群,这可以说是我每年的一个挑战,最后的那部片子中选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因素,我跟马可主席,萨布丽娜·巴拉切蒂、卡洛·沙特里安都合作过,我还是挺走运的,因为你们都对中国非常感兴趣。
不同的艺术总监关注的地区可能不一样,因为他们觉得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魅力,你们还是百分之百关注中国的,所以对我来讲跟你们交流特别有意思。为什么我给大家推荐这些片子?这些都是这一年当中非常突出的片子,可以说每年都有这么一个挑战。
观众提问环节
贾樟柯:谢谢我们的几位嘉宾,下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现在开放提问,请举手。这位男生是最早举手的。
提问:我想问一下戛纳跟柏林的两位选片人,因为今年威尼斯电影节把金狮奖颁给了超级英雄电影,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然后再加上像2017年的时候,当时金狮奖也是一部偏商业类型的电影(《水形物语》),我想问一下,现在三大电影节是否有更向商业电影和更向观众喜欢的这些通俗电影妥协?
然后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因为法国这两年也产生了新兴浪潮,就像2017年的《野小子们子》,还有2018年的《刺心》,现在就是感觉一帮很激进的年轻电影人在颠覆传统的电影类型,当然也颠覆了很多像三大电影节的那种保守价值观,对于这种状况你们是怎么看的。谢谢!

卡洛·沙特里安:你说的《水形物语》,还有《小丑》,都是威尼斯那边颁的奖。我不是评判威尼斯,威尼斯每年都在这么一个独特的时刻举行;去年、前年,他找到了自己的方式,然后找到了一个很大的空间给美国电影。
《寄生虫》也表现非常好,但也不算是商业大片。我并不觉得这有一个趋势,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电影的力量很大,而且由于奥斯卡的影响,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也就是威尼斯,还有像多伦多,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给美国的影片腾出了很大空间,你说他好也行,说不好也行,但是他们的市场力量确实很大。
在柏林这边我不想多讲,因为我还没开始我的工作。作为影评人或者观众的角度来讲,视角都不一样,柏林那边也都会每年展映美国电影。
关于颠覆电影的拍摄方式,总有年轻的电影人他们想要打破陈规,这是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们就是要找到新的声音,新的叙事的方式,包括市山尚三先生也讲到了这一点,他也有很大的发现,我们就是期待不断有人去打破,有新的东西出来,在法国电影当中我觉得可能这方面做得还不是特别足够,少了一些。

克里斯蒂·琼: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趋势,我觉得是一个个人的行为,有的人更颠覆一点,有的人更保守一点,不存在什么浪潮或趋势,在某些国家有一些年轻人喜欢颠覆,甚至搅乱搅扰一些比较保守的趋势,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提问:我是来自重庆的一名观众,想问一下我们的平遥国际电影展是不是每年固定在一个时间段进行展映,还有在什么媒体能看到关于展映的内容,因为我们这一次过来也是非常无独有偶,所以我们也想身边的朋友,喜欢电影的朋友,能对这个电影展进行长期的关注。第二个问题想问一下贾导方不方便透露一下关于新片的计划。谢谢!
贾樟柯:那我简单说一下,平遥国际电影展每年国庆节后第一个星期四开幕,每年都会举办,如果钱还够的话。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官方的网站,这个网站一年四季都会更新,我们也有众多合作的媒体,有关影片的征集、节目单、片单、购票方法、产业的报名,包括我们产业项目的这种发布,都会在官方网站合作的这些媒体及时地发布。然后有新片刚刚完成,正在后期制作之中。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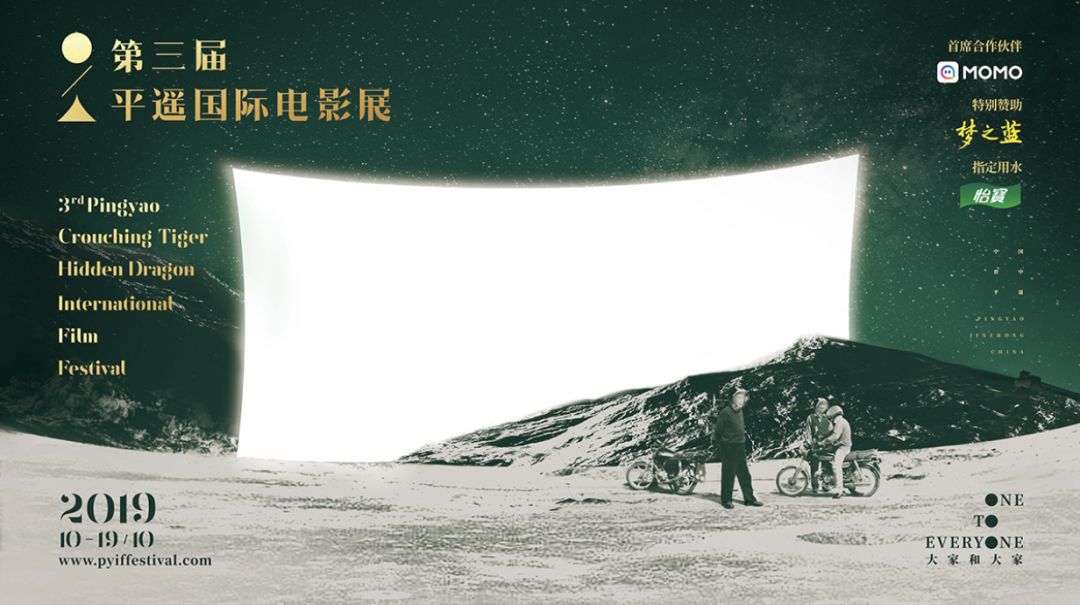
提问:我有一个可能对于很多新导演做第一部片子都很实际性的问题。我们在投国际影展的时候一般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是因为成本的问题,如果我有选片人的联系方式,我可以直接去联系,或者说当我有这部分的预算,我是跟一个代理商,他来帮我做更好的计划,然后再统一投递各种影展。我想知道对于成本有限的新导演来说哪个方式会更好一些?
本杰明·伊洛斯:很简单,你用第一个办法,就是你如果能联系到选片人,你就直接联系他。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中国电影界现在有这样的情况,有些导演过于注重自己电影的镜头,注重表达方式,注重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却忽略了观众的思想,导致他们的片子在观众看来可能比较冗长,并且可能会不知所云,无法感受导演的意思或导演他想表达的创意,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
基里尔·拉兹洛夫:很简单,多种多样的电影都是应该存在,应该在一起竞争。不管是电影节,还是在其他的环境下,所以没有什么一定的规定。有一些电影作者他不去想评论,或者是不在乎观众怎么想,他可以去博物馆或者大学放映,有那么一些导演到最后终于获得大的承认,人们认为他是大艺术家。我们需要看时间。

提问:贾樟柯导演您好,各位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一些新的想从事电影或导演方面的人面临很多问题。相信你们曾经也遇到过,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很不容易有拍摄的资金,或者说可能在艺术方面他有自己的一些坚守,但是在实际中可能很难达成自己的一些想法,要么就去妥协;或者说想找一些平衡点是非常艰难的,这些情况在我身边,包括朋友也遇到了很多很多,他们有挣扎,想妥协,但是可能还是拿不到资金。
我想问一下,特别是贾樟柯导演,以及现场那么多的电影界的专家,你们有没有可能对新的导演有一些扶持或者资金支持计划,如果有的话,你们是通过哪些机制或者平台。因为我是重庆人,贾导的片子很多都在三峡,就想问你对三峡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情感。谢谢!
贾樟柯:好,我首先声明一点,从这个问题之后不要再问我了,因为我是主持人,这几位这么远来,机会难得,应该多问他们,所以涉及我的问题简短回答一下。我们平遥国际电影展今年开始创办了创投,我们今年的创投是剧本的创投,你只要有一支笔有一张纸能把剧本写出来,投递到平遥国际电影展,今年我们收到了506个项目,从这506个项目里面我们就竞选了16个项目。
这16个项目里面分成三个类型,一个类型是已经有过电影实践的,有作品的导演;有一个类型是拍过一些短片,或者说有过其他电影经验的,比如在剧组工作过的;另外一部分就是完全没有电影经验的,在这16个项目里面各占有很大的比重。
我们有一个初评的小组,他们认真地读这些剧本,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机制,这个机制不仅在平遥,在全国,包括十二月要举办的海南电影节,六月的上海电影节,他们都有这个,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机制吧。另外一个就是缘分,有一些制片公司碰到大家了,拿到剧本了,可能就会促成合作,这个没有什么规律,更重要的是机制的建立。我很爱三峡。
提问:大家在选片过程中有遇到什么非常困难的时候吗?关于片子(的挑选)。
克里斯蒂·琼:我觉得大家都差不多,就是在选片的时候我们得看大量的片子,所以怎么把他们筛选出来,这个挑战是挺大的。我们的工作就是让片子尽量多样化、多类型化,比如我们认为在一年的某个时刻这个电影是特别有表现力、代表性的。有的时候我们有心头所好,但是无法选它,可能我们选的电影并不是特别喜欢的那一部,但是还是要为了多样性的原因把它选出来。
贾樟柯:好,谢谢大家!最后讲到了选片是秉承多样性的原则,谢谢今天我们几位嘉宾的分享,也谢谢观众朋友,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几位一起来留个影。好,谢谢大家!

